驛馬車
 昨天是個特別的日子, 我們正式和開了十一年的車說再見.
昨天是個特別的日子, 我們正式和開了十一年的車說再見.
來紐約以後的第一輛車是Toyota Celica 三門車, 那時是學生, 和朋友買來只花了美金二百元, 從這個價錢可以想像車子的破舊程度. 車子的冷氣不行, 雖然有暖氣, 但廢氣會從車底破洞跑進來, 於是冬天就要面臨開窗凍死, 或者關窗悶死的兩難抉擇. 更好笑的是某一個嚴冬, 鑰匙凍在門鎖上拔不出來, 雖然有備份鑰匙, 但是從此車門上就插著那把 “石中劍”, 誰要能像亞瑟王一樣把它拔出來, 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車開走.
這輛小車雖然不起眼, 卻還蠻能跑, 讓我們初嘗 “有車階級” 的滋味. 說實話, 住在大眾運輸發達的紐約市, 擁有一輛車的負擔遠超過車子所帶來的便利. 除了塞車, 停車也是一大問題, 停車場的費用不是學生所能負擔, 即使在街上找到停車位, 還得一大早起來忙著換邊停車, 以應付市政府每週三次的掃街 (每次只掃街的一邊).
開了二年左右, Celica竟然被偷, 找回時已不堪使用, 於是貸款買了一輛新車.
有車雖然麻煩, 但讓平日在地鐵中鑽進鑽出的土包子, 有機會探索紐約市外的廣大世界. 從住滿中產階級的郊區和大型購物商場, 到滿佈湖泊山林的州立公園, 我們開車越走越遠, 沿著95號州際公路, 向北穿過新英格蘭的大城小鎮, 到加拿大的魁北克; 往南經過華盛頓特區, 一直到佛羅里達州的最南端.
就像以前穿越北美往西部遷徙的拓荒者, 這輛塞滿帳篷睡袋的Toyota Camry 是一個活動的家, 也是載著我們 “發現美國” 的驛馬車. 每次到野外露營, 萬籟俱寂, 只要藉著星月餘光分辨出車子的輪廓, 就覺得週遭的環境不再陌生, 黑暗也不可怕了.
對我們而言, 車就像一個忠實的老朋友, 上面所承載的, 豈僅是帳篷睡袋而已. 每次長途旅行歸來, 都會伸手拍拍車子, 意思是說: “辛苦你了”.
 一年年過去, 車上里程表的數字也越來越高. 有一次在回台灣的飛機上, 盯著螢幕上的里程數, 驀然發現車子走過的路等於環繞地球十圈, 遠遠超過了紐約到台北的距離.
一年年過去, 車上里程表的數字也越來越高. 有一次在回台灣的飛機上, 盯著螢幕上的里程數, 驀然發現車子走過的路等於環繞地球十圈, 遠遠超過了紐約到台北的距離. 如同年輕的時候不會考慮老死, 開新車的時候也不會去想車子的使用年限. 然而十一年後, 累積了三十萬英哩 (五十萬公里) 的老車, 讓我們不得不面對這問題.
難捨的心情當中, 我們再也無法忽視如坦克車般的噪音以及排氣管冒出的刺鼻廢氣, 可能對環境造成的損害. 拿到修車廠去, 連車廠老闆也說: “該換車了, 就算花錢也很難修好. ”
“也許到鄉下買塊便宜的地, 蓋一間車房, 讓老車在那裡休息吧? ” 有時在討論如何處理車子之際, 這個浪漫的想法會湧上心頭.
“開了那麼多里程, 搞不好豐田汽車會頒一個獎章給我們? ” 另一個更不實際的想法.
當車子的里程接近三十二萬英哩的時候, 我們決定把它捐贈給慈善機構.
車子被拖走的時候我不在, 但是那若有所失的感覺卻縈繞不去.
我所丟棄的, 不僅僅是外面包著板金鐵皮, 裡面配備油箱引擎的機器. 也包括了第一次野營的雀躍, 初到一個未知城市的好奇, 在陌生之地到處找路的惶惑不安, 還有剛剛畢業, 開始工作的那段黃金歲月.
不捨棄舊的事物, 哪能獲得新的東西? 然而曾經捨棄的, 豈只是這些?
坐在驛馬車上, 眼睛總是向前方張望的我, 第一次回過頭去凝視身後的風景... 那一路上散落在荒煙蔓草間, 和家人朋友相處的點點滴滴, 以及成長中曾經珍視過的記憶與心情, 都再也回不來了.
也許, 是該下車步行的時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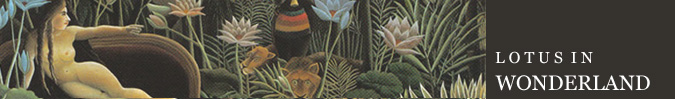

Comments
真是好文
真是感動....
整天不知怎麼安頓的心情,到這裡讀了幾篇後都好像能沉澱下來了....如墜入深海的寧靜...
Posted by: 篤 | April 28, 2007 11:42 AM